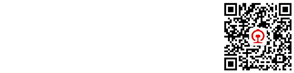【摘要】中国已全面进入高铁时代,高速铁路在可达性、交通距离和时间成本方面的巨大潜在优势,必然对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模式、形态与格局产生持续的系统性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对中国的区域格局、人口流动、第三产业和旅游发展已然产生了系统性的重要影响。总体上,高铁的引导、促进、辐射、联动、重组等正面机制与作用日益凸显。随着中国“四纵四横”主要高铁网的规划与建设不断加快,高铁对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全面重塑工程也将越发深入。
【关键词】高速铁路 空间格局 人口流动 第三产业 旅游业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2.002
高铁对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
理论与实践表明,高铁对加速区域一体化,推进城市群内部节点的性质与功能调整,强化城市群之间相关节点的功能联系,以及提高区域经济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关于高铁如何影响区域空间格局,我们采取了新的技术路线,一是根据国际上关于高铁的竞争半径的经验研究,我们以500~1000km为辐射半径,首先制作中国高铁时代的“多中心地图”;二是将高铁视为时间距离和时间成本的一种压缩工具,在方法上以“时间距离”替代“空间距离”作为决定城市群乃至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核心要素,并借鉴二维扭曲时空地图(2D Shrinking Time-space Maps)的方法论体系,制作“时空压缩地图”,来研究高铁对中国区域时空格局特征的影响。
高铁对中国区域总体格局的影响。在方法上,首先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五个中心城市作为基准点和高铁经济区的核心,并保持其地理坐标不变;然后,在五个高铁经济区范围内选择26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再分别计算所有城市节点到五大核心的最短通达时间,完成“空间坐标”向“时间坐标”转化。时间距离变化计算显示:(1)高速铁路建成后,时间节约1/3强。经过模拟,高铁建设前各节点通达五个中心城市的总时间为1101.0h,建成后的总通达时间压缩至723.5h,节约时间377.4h,约占原通达总时间的34.3%。(2)高铁的网络化建设对时间距离的压缩效果显著。以2011年末作为现状的时间节点,2012~2050年建成的高铁对时间的节约由现状的1/5强增至1/3强,节约的时间由现状的232.3h增至规划期末的377.4h;覆盖的城市增至153个,约占覆盖区264个城市的58%。(3)高铁对不同范围内节点通达性的影响差异显著。将各节点高铁规划前和规划后到达五大基准点的通达时间(0~20h)分别进行排序,与“节省比例”(节省的通达时间/无高铁状态下的总通达时间)(0~100%)进行对比,发现:第一,各高铁经济区范围内,总体上由“昼夜兼程”演变为“朝发夕至”或“夕发朝至”。例如乌鲁木齐至重庆的时间由18.8h压缩至9.2h,“节省比例”=51.2%;拉萨到重庆的时间也由18.9h压缩至12.9h,“节省比例”=32%,成为“边缘城市”。第二,中远期高铁的规划建设,并未使五大基准点城市相邻节点的通达性得到明显提高。例如,统计的28个“节省比例”=0.0%的城市,按照“规划前”的时间排序,多数分布在“通达时间”=4h范围内,并密集分布在“通达时间”=2h范围内;相反,按照“规划后”的时间进行排序,其“通达时间”=0h的城市分布相对均衡,尤其集中在“通达时间”=2h范围内的节点明显减少。
由此,意味着以五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2h经济圈以内的相邻节点,其通达性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原因是高铁沿线节点通达性迅速提高,致使“节省比例”平均集中在50%上下。而非高铁沿线的城市,若考虑到转乘时间,时间成本仍相对较高,旅客将继续借道高速公路与中心城市保持联系,使该类城市成为“高铁完全覆盖区的死角区域”,如承德、肇庆等。2h经济圈以外,各节点的“节省比例”则集中在30%~40%,并逐渐下降,意味着通过转乘,高铁对时间压缩的价值明显降低。同时,该范围内节点的“节省比例”具有相似性,两极分化特征弱化;少数几个城市的“节省比例”=0%,如十堰、襄樊、赤峰、邵通等非高铁覆盖区域,通过转乘高铁的时间成本反而提升,使该类城市成为“高铁不完全覆盖区的死角区域”。
通过时间距离变化的计算,高铁时代中国总体的区域空间格局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全国264个节点城市明显地由相对分散演化成绝对集中的分布特征。如果按照既定的设定,全国形成了5大高铁经济区。其中:北京高铁经济区内,京津冀和济南都市圈联合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城市集聚区”、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城市集聚区”,哈大线则集中了蒙东、哈大长、长吉图的几个城市,线性特征明显强化(如图1所示)。合肥—武汉的高铁穿越大别山(黄冈市麻城)延伸至宜昌,影响区内集中了中原城市群诸多城市,使传统的、南北向的、线状集聚特征明显的郑州—武汉沿线的京广铁路城市集聚区,形成了组团式的、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集聚区”。上海和广州高铁经济区依托发达的综合交通网络,使之成为城市集聚程度最高的两大都市连绵区。其中,海西经济区通达广州的时间由5~6h压缩至2~3h,“节省比例”=40%~60%,而南北钦防四城市通达广州的时间由3~5h压缩至2~3h,“节省比例”=30%~40%,“泛珠三角城市群”廊道效应凸显,形成了海西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和珠三角城市群三大国家政策区联袂发展的“中国南部沿海经济区”。
第二,线性特征的增生与退化并行,传统的“T字型”或“π字型”等线性特征逐步消逝,使之成为高铁对中国总体区域经济格局最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线性特征的退化突出表现在兰州—乌鲁木齐高铁的规划建设将使天山北坡的七市四县和四个兵团通达内地的条件发生革命性变化,“边疆变内地”,沿边各地区通达重庆的时间均压缩50%以上。线性特征的增生突出表现为“呼伦贝尔—哈尔滨”线性特征的凸显,原因在于蒙东部地区缺乏南北相连的高速公路,而对接哈尔滨的绥满高速尚未全线通车,因此,呼伦贝尔转到哈尔滨至北京的价值被弱化;鸡西、牡丹江和七台河等亦为此状,使之成为“高铁非完全覆盖区的死角城市”。
高铁对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
高速铁路降低了地区间人口流动的交通成本,缩短了地区间的时间距离,扩大了核心区域的影响半径,必将加速人口的流动速率,助推城镇化发展速度。而且高速铁路通过新站点的建设、铁路线的增设,或将影响现有人口流动的强度与方向。本文以“京沪高铁”为案例,根据各地级市人口统计年鉴数据,将流动人口定义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分析高铁对区域人口流动的影响。
高速铁路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效应。第一,京沪高铁沿线站点城市流动人口密度显著较高,无论绝对值或增幅均高于非站点城市。非高铁站点流动人口密度从9.28人/平方公里(2000年)增至24.62人/平方公里(2011年),增幅15%;高铁站点从39.67人/平方公里(2000年)增至109.9人/平方公里(2011年),增幅17%。结果说明,人口流入在高铁站点尤为显著,交通区位与人口流动方向、规模具有正相关性,两者间具有正向的互动效应。
第二,高铁加剧了站点城市流动人口的集聚或疏散效应,起到了人口流动的“管道”作用。为探究高铁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效应,我们按人口流入或流出方向分类,将高铁站点、非高铁站点城市细分为“人口集聚型站点城市”“人口疏散型站点城市”“人口集聚型非站点城市”“人口疏散型非站点城市”等四类城市。研究发现,人口流入的高铁站点,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人口持续流入,年均增长率为17.8%,人口流入的非高铁站点城市,11年间仅维持平稳小幅上升,年均增长15.7%;原属人口流出的站点城市11年间人口净流出增幅24.1%,而非站点城市仅为16.3%。
第三,高速铁路对人口的吸引效应具有一定区域辐射特征,京沪高铁对流动人口影响具有空间扩散及虹吸效应。分析发现,高铁站点及50km以内的城市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性,站点人口密度从39.7人/平方公里(2000年)增至109.9人/平方公里(2011年),增幅16.1%;半径小于50km区域人口密度从10.4人/平方公里(2000年)增至87.0人/平方公里(2011年),增幅67.3%。京沪铁路对半径大于50km、小于100km区域人口密度则具有较强的人口虹吸效应,2000年区域净迁出10人/平方公里,2011年增长16.26人/平方公里。大于100km区域,2000年人口为净流入(32.7人/平方公里),2011年净流入下降至15.88人/平方公里,人口更多地流向交通更先进、经济更发达、就业机会更充裕的地区。
高速铁路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制。基于2006~2011年京沪高铁沿线人口流动及相应经济社会面板数据,建立以“高铁站点区域”“高铁开通与否”为分组标准的双重差分面板回归。结果显示:(1)人口流入与预期收入、生活成本、产业结构具有显著性,验证了传统人口流动理论。(2)高铁站点城市与非高铁站点城市,高铁辐射区域与非高铁辐射区域相比,具有较高的人口净流入,与统计分析相符。(3)高铁开通对高铁站点及区域的人口流动直接影响不显著。
由于“高铁开通与否”对人口流动的直接影响效应的研究结果不显著,需要分析高铁是否存在对人口流动的间接效应。根据国外文献关于高铁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综述,我们主要选取地区人均GDP、第二/三产比重为中间影响变量,研究高铁是否通过提高地区人均GDP、提升地区产业结构,以此间接吸引人口流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人均GDP与劳动就业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显著相关,在高铁站点具有较强的发展水平,并在高铁开通后有明显的提升。(2)第二、三产比重与高铁开通并无明显相关性。
由此可推测,高铁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高速铁路站点的设置提高了区域可达性,降低了人口流动的时间、交通成本,提升地区可达性,直接提升了人口净流入;另一方面,高铁在不改变地区产业结构的同时,增强了区域间信息技术、人力资本的交流强度,直接作用于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变量,提高了地区人均GDP产出,由此间接地提升了地区收入预期,对人口流入具有积极影响。 |